【每个人都了不起】“画医”周志杨:在时间的轴里对话
这是周志杨普通的一天。
大大的案桌上,一幅百年前的书法作品正在被“医治”,用水整平、上保护纸、刮平、揭覆褙、打局条、上浆糊、拓画芯……
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,全神贯注带来了十分的静谧,工作室里,静得可以听见人的呼吸声。
“这些古人早不在了,但是我处理他们的作品,就感觉是在与他们对话。”周志杨如是说。这样的对话,周志杨进行了三十多年。
从19岁学徒,到如今年过半百,周志杨入了这一行,就执着这一行。一生只为一事来,他说,自己乐在其中。

(一)
明代周嘉胄有言:“古迹重裱,如病延医,医善则随手而起,医不善则随手而毙。”
对此,周志杨深有感触:“字画修复,很考验人的耐心和细心,一个不小心,这个作品就废掉了。”而这,也是他从师傅那儿学到的第一课。
周志杨至今记得,19岁的那个夏天,在表哥家店铺的隔壁,他第一次见到师傅的情景。彼时师傅已经80多岁了,坐在案桌前静静地揭裱着一幅古字画,周围那么嘈杂,却丝毫不受影响,以指为刀,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揭去破损的裱褙。“那一刻,我就被师傅的手艺打动了,就想跟着学。”
周志杨的师傅叫夏振印,是东台夏氏装裱第五代传人,尤擅修复揭旧,一生装裱、修复古今名家如郑板桥、岳飞、唐伯虎、范曾等字画逾千幅。很幸运,周志杨成为了夏振印的关门弟子。当然,初识师傅,周志杨并不知道这些,他更多感受到的,是师傅的严谨、细致。“有时候,一天只能揭巴掌大的地方,有的作品,要个把月才能弄好。”
“宣纸一下水就软了,你手法出一点错,纸就烂掉了。”初学拓宣纸,周志杨有点摸不着头脑,明明很细心了,纸却还是破。技术的娴熟,还是得靠练。宣纸舍不得浪费,就用旧报纸,十次、百次、千次……两年的时间里,周志杨练掉了上万份旧报纸。
时间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,今天周志杨所走的每一步,都离不开当年努力练习的每一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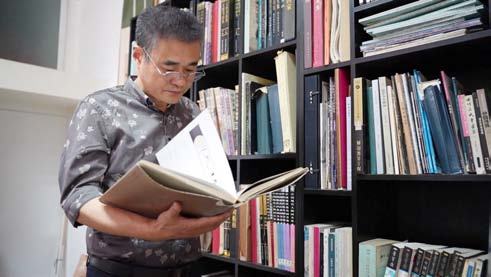
(二)
采访这天,周志杨处理的是一幅清中期的行书作品,前阵子网上一位客户刚寄过来,请求再次装裱。时间,让这幅作品饱经“沧桑”,裱褙残缺不谈,作品本身还有多处褶皱、破洞、污迹。然而,在周志杨看来,这已经算是好的了。只需要修旧如旧,做轻微的“小手术”就可以。
绢保八百,纸寿千年,但是保存不当,亦会让作品受损。周志杨表示,有时候拿到的作品受潮发霉、鼠咬虫蛀、轴朽断裂,甚至是画卷都破成碎块,画芯都有残缺。“这种作品,就得重新揭裱、补褙,等于一次‘大手术’。”
去年周志杨就修复了一幅清末“海派四大家”之一吴昌硕的花卉作品。当周志杨拿到手时,几乎就是一些破碎的纸片,而且作品受潮严重,不少地方都霉烂了。沉进去,慢慢来,周志杨没有泄气,接下来的数日,他几乎“钉”在了工作台,架起老花镜,刷子、镊子不离手。大致的模样整平,揭褙,碎片儿一个个去拼齐,发霉的地方则细细去污。“那些破损的地方,我就根据原来作品的风格,去调颜料,补起来。”
这幅作品,周志杨前后忙碌了一个多月,当作品再次装裱,重现光彩,周志杨细细端详了半天,不仅被吴昌硕作品那“奔放处不离法度,精微处照顾气魄”的金石气所折服,更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成就感。
在周志杨看来,时间带来的伤痕,亦可以用时间去修复,这个时间,一点儿也不能“担待”。虽然一锅用干面熬的浆糊得花几个小时才能制成,但是它可以重复揭裱,延长作品的生命力,而且不伤作品,所以,他从不用工业浆糊。虽然揭画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腰背都酸疼,但指尖功夫一点马虎不得,坐着揭,站着揭,轮流换着。
这些年,周志杨修复装裱过郑板桥、唐伯虎、李复堂、林散之、赵朴初、费新我、启功、陈大羽等古今名家字画,在和一幅幅作品的对话中,周志杨提升着、熏陶着、快乐着。
(三)
对于周志杨来说,最为开心的则是接手东台书画家的作品。
在工作室的二楼,陈列着他修复过的一位位东台地方乡贤的书画作品,鲍审的《牡丹图》、古培寿的《竹园夜读册页》、陈汝玉和周应芹合作的《报喜图》、朱闰的《结伴会知音》等等,此外还有不少曾寓居或宦游东台的文人作品,如韩国钧、朱沆、沈子丞等。“这些都是东台的文化荣光。在几十年前、一百多年前,东台的书画氛围就很浓厚了。”周志杨表现出的自豪溢于言表。他说,每次修复装裱东台人的字画,都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。
也许,正是因为这种书画氛围,和书画相关的装裱技艺,在东台也是传承不息。周志杨工作室的三楼操作间,虽然鸦默雀静,却充满着“活力”,因为,这里有不少年轻的徒弟。“我已经有几个徒弟学成,自立门户了!”周志杨说,在他看来,中国书画之所以能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,装裱和修复技艺真的很重要。
当然,和所有的工艺一样,传承和创新,缺一不可。重要程序纯手工外,周志杨也将“现代元素”加了进来。比如湿纸、裁剪等等。“我现在还在尝试立体装裱,装裱的风格也作了一些改变。”周志杨说,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,使得书画作品可以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。(陈美林/文 杨阳/摄 杨心乔 杨烨霏)

扫码看视频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