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寺铁火(上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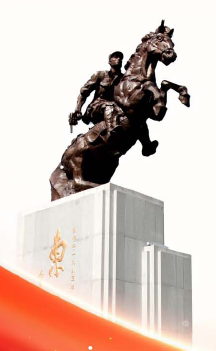
引子、麦田深处的红色印记
初夏的风拂过苏中平原,无边的麦浪翻滚着金黄,空气中弥漫着谷物成熟的芬芳。在这片象征着丰收与安宁的土地上,两位年轻的党史工作者,循着泛黄档案中的零星线索,来到了一个名为绍河庄(现三仓镇仓胜村)的静谧村庄。
村庄深处,一座飞檐斗拱的古寺静立其间,与周边崭新的民居相比,显得格外古朴甚至有些破败。青砖斑驳,木门吱呀,唯有庭院中那棵需两人合抱的参天古银杏,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领路的村党总支书记,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人,指着古寺后殿一片不起眼的空地,语气深沉:“就是这儿了。当年,你脚下踩的这块地方,白天堆着煤炭和铁料,晚上可是炉火通红,叮当声能响到后半夜哩。”
他转身又从村委会的柜子里,郑重地捧出一个褪色的布包。层层打开,里面不是经书佛像,而是几件锈迹斑斑的实物:一个形状奇特的铁砧,半截磨得极其纤细的钢锉,还有一块黑乎乎、疑似熔炼残留的矿渣。
“这些都是当年兵工厂留下的‘家当’,”村书记用粗糙的手掌轻抚着这些铁器,仿佛在触摸一段滚烫的记忆,“我小时候,常听我爹讲,这庙里住的不是和尚,是一群能‘点铁成金’的能人。他们能把破铜烂铁,变成打鬼子的枪子儿和‘铁西瓜’。”
年轻的考察者蹲下身,拾起那半截钢锉。锐利的尖端虽已锈钝,却依然能想象出它当年在工人手中,如何于钢铁上游走,打磨出杀敌利器的锋芒。他闭上眼,麦浪的沙沙声渐渐远去,耳畔似乎响起了历史深处传来的风箱呼啦、铁锤叮当,以及那隐没于时间长河中的火热心跳。
这座古寺,从未真正沉睡。它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,都烙着一段由铁与火、智慧与鲜血谱写的烽火传奇。正是:
古寺森森麦浪平,残砧锈锉认前盟。
犹闻风箱呼呼响,铁火曾燃彻夜明。
临危受命:烽火岁月中的战略抉择
皖南惊雷,绝境求存
历史的指针回拨到1941年。中国的抗日战争,正处于最为惨烈、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。而在这一年的一月,江南阴冷的冬日里,一声“皖南事变”的惊雷炸响,让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震惊和悲愤。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,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,突遭国民党顽固派重兵的伏击围攻。血战七昼夜,弹尽粮绝,除两千余人突围外,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,军长叶挺谈判被扣,项英遇害。这支在华中敌后浴血抗战的英雄部队,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。
消息传来,举国哗然,各界爱国人士同声谴责。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,在愤怒与悲痛中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。面对国民党当局“撤销番号”的诬令,中共中央军委迅速发布命令,重建新四军军部,将活动于大江南北的九万余名将士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,继续高举抗日旗帜,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。
正是在这风雨如晦、黑云压城的危急关头,骁将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。他与政委刘炎、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一起,临危受命,肩负起在日、伪、顽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苏中地区,坚持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千斤重担。1941年1月19日,粟裕率师部进驻东台县城二女桥,后辗转移至东部海边的三仓吴家桥。
苏中,东临黄海,南扼长江,西控京杭运河,是插向日伪统治核心区域的一把尖刀。这里物产丰饶,人口稠密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正因如此,它成为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,支援太平洋战场,在此推行了惨无人道的“扫荡”“清乡”和“蚕食”政策,所到之处,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企图以血腥手段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基础。
无米之炊,粟裕的远见
铁与火的较量,从来不只是勇气与意志的比拼,更是钢铁与后勤的角逐。对于重建不久、身处敌后的新四军一师而言,这种较量显得尤为残酷。皖南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,一道无形的铁幕已然落下——海外援助的通道被彻底封锁,国民政府微薄的补给也完全断绝。一师的战士们,几乎回到了最原始的“以战养战”的状态,每一支枪、每一颗子弹,都需用鲜血与生命从敌人手中夺取,这便是一曲广为流传的《游击队歌》中唱的“没有枪,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”,歌声背后,掩藏着难以言说的艰辛。
前线的战况,如同一条条冰冷的讯息,不断传回师部:一场恶战之后,阵地上散落着型号杂乱的枪支,“老套筒”“汉阳造”甚至土铳鸟枪,膛线早已磨平,准星歪斜。更令人揪心的是弹药,每个战士腰间那几颗金贵的子弹,被反复摩挲得光滑锃亮,非到敌人进入五十米内,绝不准击发。战斗的间隙,不再是休息,而是一场更为紧张的“狩猎”——战士们需要匍匐爬出阵地,在冰冷的尸体间仔细搜寻,只为找到几颗可能适配的子弹壳。一位老连长在战后报告中沉痛地写道:“战士们是在用刺刀和血肉,去弥补火力的不足。我们是在用生命,为下一场战斗‘筹措’军火。”
这种“叫花子打狗,边打边讨”的窘境,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牢牢束缚着部队的手脚。机动作战因弹药不济而步履维艰,巩固根据地也因火力薄弱而困难重重。一支缺乏稳定后勤保障的军队,犹如无根之萍,在敌人持续不断的“扫荡”与“蚕食”中,前景堪忧。
这一切,都被一双深邃而锐利的眼睛看在眼里,忧在心头。他就是师长粟裕。在一次气氛凝重的军事会议上,墙上的作战地图红蓝箭头交错,勾勒出苏中地区犬牙交错的险恶态势。粟裕久久凝视地图,沉默不语,与会干部都能感受到他肩头的千钧重压。
终于,他转过身,目光如炬,扫过每一位同志的脸。他没有高声斥责,声音低沉而有力,每一个字都敲击在人们心上:“同志们,我们都看到了,前线的战士们是在用什么样的条件在和敌人拼命。我们不能总是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,去硬扛敌人的钢铁!靠‘输血’过日子,终有血尽人亡的一天;当‘叫花子’,永远打不了胜仗!”
他走到地图前,手指重重地点在苏中根据地的心脏位置,语气陡然变得无比坚定:“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‘家当’!要有能为我们自己‘造血’的根基!在苏中,我们就是砸锅卖铁,也要把自家的兵工厂建起来!哪怕它一开始只是个能敲敲打打的铁匠铺,只能让老枪焕发新生,只能让子弹壳再次怒吼,这就是我们迈向胜利最坚实的一步!这不仅关乎一场战役的得失,更关乎我们能否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根,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将抗战进行到底!”
此言一出,石破天惊。这不再是困境中的无奈叹息,而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基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洞察,发出的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宏伟宣言。它为苏中抗战点燃了新的希望之火,即将诞生于古庙之中的兵工厂,序幕由此缓缓拉开。
隐秘的抉择,古寺为厂
师部的决策,需要坚定的执行者。创建兵工厂的任务,落在师供给部以及苏中军区各级领导的肩上。然而,在无险可守的平原水网地带建立一个需要稳定环境的兵工厂,其难度超乎想象。厂址的选择,必须同时满足几个近乎苛刻的条件:隐蔽、交通、群众、水源等。
它必须极其隐蔽,能够躲避敌人频繁的空中侦察和地面“扫荡”;它又需要相对便利的水陆交通,便于机器设备、原材料的运入和产品的输出;它必须紧靠群众基础牢靠的“堡垒村”,以确保信息安全和人员掩护;同时,充足的水源也是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为此,一师供给部部长罗湘涛等同志,亲自带领精干的侦察人员,化装成商人、渔民甚至乞丐,足迹踏遍了兴化、东台、宝应一带的河湖港汊。他们昼伏夜出,秘密寻访,评估着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地点。
最终,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了三仓一带的绍河庄。这里沙荒绵延,芦苇茂密,河网纵横如迷宫,敌人的装甲车进来就陷,汽艇来了就搁浅,堪称天然的隐蔽屏障。村庄规模不大,但党组织坚强,群众对抗日队伍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而村庄深处,那座名为“绍河庄庙”的古寺,更是理想的落脚点。
绍河庄庙历史悠久,殿宇较为宽敞,结构坚固。因其位置相对独立,四周有高大的树木和竹林掩映,从外部极难发现。庙产原本不少,但战乱年间香火已衰,僧人离散,正好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。经过周密的政治审查和实地勘测,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最终形成。
1941年春夏之交,一个隐秘的命令从新四军一师师部发出:立即启用绍河庄庙,筹建一师直属修械所。历史的洪流,就这样将一座祈求世间和平的古老禅林,与一个为民族解放而制造铁与火的兵工厂,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风雷激荡的时代,为这座古寺赋予了全新的、充满硝烟与热血的使命。正是:
皖南惊雷,江河裂、孤军浴血。
望苏中、倭寇逞凶,封锁如铁。
将士摩挲弹五发,沙场匍匐寻残械。
问苍天、何日铸长缨,诛妖孽?
庙堂策,心如铁;兵工事,从头越。
纵白手起家,志比钢烈。
古寺权当兵甲地,梵音化作锻锤节。
待来日、铁水化洪流,吞残月。
古寺新生:创业维艰百战多
当重建军部的命令传遍华中,当一师将士在苏中大地浴血坚持时,一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队伍,正悄然进驻绍河庄那座荒寂的古庙。他们肩扛手抬的,不是经卷,而是沉重的铁砧、风箱和几箱最简单的工具。古老的禅寺,即将迎来它命运中最为喧腾,也最为神圣的篇章。
白手起家:庙堂里的“手工作坊”
第一批军工战士推开绍河庄庙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破败:院中荒草没膝,大殿内佛像蒙尘,蛛网纵横,唯有几只受惊的野鸽扑棱着翅膀从房梁飞走。寂静,是这里唯一的主题。
厂长姓李,这位曾在上海机械厂工作过的“技术权威”,放下行李,走到大殿中央,用脚踩了踩坚实的青砖地面,声音洪亮地对大家说:“同志们,这儿,就是咱们未来的‘高级兵工厂’了!别看现在空荡荡,要不了多久,这里出的家伙,够鬼子喝一壶的!”
他的话引来一阵笑声,驱散了初来者的迷茫。笑声过后,是更为现实的严峻。全厂的“家当”一一摆开:一个需要两人才能拉动的巨大木风箱,一个几十斤重的生铁砧子,几把大小不一的铁锤,以及锉刀、老虎钳、台钳等手工工具。没有一台靠动力驱动的机器,没有电,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工棚。
“车间”就地设立。大殿成为主厂房,锻工炉靠着原本的香案砌起来,铁砧安放在佛像前。东西厢房,一间作为钳工房,另一间则作为仓库和宿舍。所谓的宿舍,就是在冰冷的地面上铺一层干草,再展开随身携带的薄被。
工作立即开始了。前线送来的损坏的枪支堆在墙角,有的枪管炸裂,有的撞针断裂,有的标尺遗失。修复它们,全靠一双手。没有车床来车制新撞针,老师傅就挑一根合适的钢条,固定在台钳上,用粗细不同的锉刀,一下一下地手工磨出形状,再精心淬火。没有膛线机,对于膛线磨平的枪管,一位老工匠想出了“土拉线”的法子——用一根细钢条,一端固定住一个用金刚砂和油调制的“磨头”,手工在枪管内来回拉动,一点点地“啃”出新的膛线。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,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枪管报废。
夜晚,古寺里亮起了昏暗的油灯和松明灯。炉火在需要锻打时才被点燃,以节约珍贵的煤炭。风箱呼啦呼啦地响着,将炉中的铁块烧得通红,然后被钳出放在铁砧上,在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中改变形状。锉刀摩擦钢铁的“沙沙”声,则如同夜曲从不间断。这座祈求宁静的寺庙,此刻正用最原始的节奏,为前线的胜利奏响激昂的序曲。
人才汇聚:干中学,学中干
兵工厂的人员构成,生动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。核心是少数产业工人,以及几位特殊人物:原是中学化学教师的陈知耘,戴着厚厚的眼镜,负责火药研制;曾在南京兵工厂干过的老钳工赵根生,话不多,但手艺精湛。
而工厂的主体,则是来自苏中本地的热血青年。他们中有的是村里的铁匠、木匠,有的是只会种地的农民,甚至还有几位是偷偷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女学生。文化水平差异巨大,但所有人的学习热情都如同熊熊的炉火。
这其中,来自当地仓胜村的王尤洪、王尤宝兄弟,是尤为突出的技术骨干。据当地老人陈龙芳回忆,哥哥王尤宝性格沉稳,精于钳工和装配,对枪支构造有极深的理解,任何复杂的机械故障到他手里,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弟弟王尤洪更富冒险精神,在锻工和简易机床操作上很有心得,善于利用有限的工具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兄弟二人进入兵工厂后,很快便在各自岗位上展现出过人价值。王尤洪凭借细致的观察力和灵巧的双手,负责最关键也最烦琐的枪械修复和校检工作。他能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,依靠手感和小土造工具,将修复后的枪支精度调整到可供实战使用的标准。王尤宝则活跃在工具革新和生产环节,他和工友们一起,想出了用“翻砂造型”配合“手工修锉”来批量制造手榴弹拉火管中的金属压板,这个办法虽耗时费力,却解决了手榴弹生产的核心难题之一。
工厂迅速开展了“包教包学”“以老带新”的活动。李厂长在庙墙上用木炭画出枪械解剖图,赵师傅手把手地教青年们如何正确使用锉刀,如何掌握淬火的“火候”。王尤洪的耐心讲解,王尤宝的亲手示范,都让复杂的工艺变得易于理解。一位叫王栓柱的年轻铁匠,性子急,锉出的零件总是不合格。赵师傅把他叫到一边,拿出一个自己锉得光滑如镜的零件让他摸,说:“栓柱,咱们手里磨的不是铁,是前线战士的命。你这里多个半丝(0.05毫米),枪可能就打不响。”王栓柱看着老师傅布满老茧的手,眼圈红了,从此沉下心来,成了厂里有名的“慢工出细活”的标兵。
文化高的帮助文化低的认字、算数。陈知耘甚至开办了“扫盲班”和“初等化学班”。在这种互帮互学、教学相长的火热氛围中,一大批“土专家”迅速成长起来。他们可能说不出深奥的理论,但凭借苦练出的手感与经验,成为修理枪械、制造弹药的行家里手,为兵工厂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
技术攻坚:“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上!”
“自力更生”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。面对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,军工们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。
“木轮”带动的车床。 修理工作很快遇到了瓶颈,许多零件无法用手工精确加工。必须有一台车床。几位老师傅聚在一起,日夜琢磨。他们从敌占区秘密购来一个废弃的汽车变速箱和一些旧皮带轮,又请村里的木匠用硬木做了一个巨大的主动轮。没有电动机,他们就在院子里砌了一个墩子,装上摇柄,由两名壮实的工人像推磨一样,轮流推动木轮旋转,通过皮带将动力传到变速箱,再带动夹持零件的主轴转动。一台“人力驱动”的土造皮带车床就这样诞生了!虽然转速不稳,加工精度有限,但它标志着兵工厂从纯粹的手工修理,迈进了机械加工的门槛。当第一个按照图纸车制出来的、闪闪发光的铜质枪栓从这台“功勋车床”上取下时,整个工厂都沸腾了。
“火柴头”里提炼的发射药。 复装子弹需要发射药,来源极其匮乏。陈知耘带领他的小组,开始了艰苦的摸索。他们最初尝试将缴获的劣质火药进行提纯,但风险极高。一次小规模爆炸,险些毁了他们的“实验室”。后来,他们盯上了火柴头。收集来成千上万的火柴,小心翼翼地刮下火柴头上的氯酸钾混合物,再与自制的木炭粉按比例调配。这个过程同样充满危险,且产量极低,往往忙活一整天,得到的火药只够装几十发子弹。但就是这几十发子弹,也是前线战士们的宝贝。
“桐油”淬出的钢火。枪械修理中,热处理(淬火)是关键一环,决定着零件的硬度和韧性。标准的冷却油无处可寻。老师傅们试验了能找到的所有油料:豆油、猪油、牛油等,效果都不理想。最后,有人提议试试桐油。几次失败后,他们终于掌握了桐油淬火的独特温度和技巧,处理出的撞针、弹簧等零件,质量竟然相当稳定。这个“土法”很快在苏中的军工部门推广开来。
正是在这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,绍河庄庙兵工厂的能力不断提升。从最初只能简单维修枪支,到能够复装子弹、制造手榴弹和地雷,这座隐藏在古寺深处的“手工作坊”,正在战火的淬炼中,一步步成长为支撑苏中抗战的坚实堡垒。一种不畏艰难、勇于创新的“铁火精神”,在这叮当的锤响和闪烁的炉火中,孕育成形,并愈发闪亮。正是:
古寺新开兵工厂,廿人创业倍艰辛。
风箱呼啦炉火旺,铁砧叮当兵器新。
锉刀细细磨星月,膛线深深刻战云。
尤宝尤洪兄弟在,巧手修得枪械神。
木轮转动皮带颤,土造车床亦建功。
火柴头上取火药,桐油缸里淬钢锋。
栓柱学艺知责任,师傅传技见赤忠。
最是古寺明月夜,锤声阵阵震长空。
编后:本文两位作者分别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(省行政学院)二级教授、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。文中核心史料参考了《苏中抗日根据地军工史》《新四军一师战史》,并融合了《红色印记:抗战中的三仓镇仓胜村新四军一师榴弹厂》,(《铁军纵横》2021年第10期)《红色档案整理:追寻抗战中的新四军一师榴弹厂》(《档案与建设》2023年第11期)等研究成果,源于历史真实,加上作者的实地察访,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。本报特分上、下两部分刊载,以飨读者。(王世谊 袁航)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