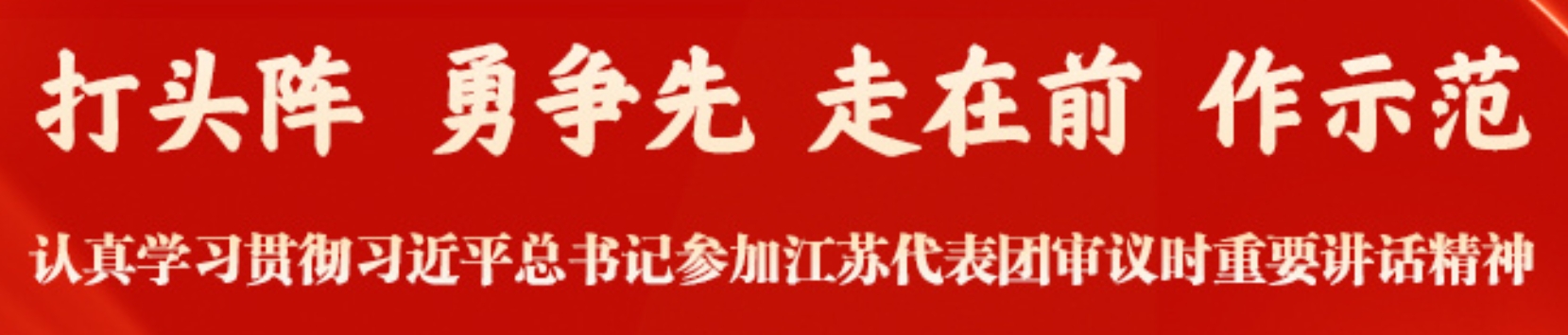抬屋
何仁湖
遇到人多嘈杂、声音过大,人们会说“能把屋子都抬了”。说到抬屋,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农村人都经历过。那时我年纪尚小,多是跟着看热闹,抬得不多,却看得真切。
在上世纪70年代末,为了兴修水利,实现连片耕作,农村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搬迁热潮——将分散的农户迁至统一的农庄线上。其规模之大,涉及面之广,可谓史无前例。仅我们许河镇,搬迁就涉及约一万户人家。这对改变农村面貌、发展生产、方便生活意义深远。
抬屋过程看似简单,实则每个环节都需缜密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先是规划选址,农庄线多选在东西走向的河边,既方便农户取水,也便于后续通电、通广播。多数农庄线规划前后两排,户与户之间间隔20米左右。直到现在,许多地方仍保留着这种布局。
选址定了,就到了宅基地安排。乡亲们为人朴实,遵照“就近”原则,谁家住前排、谁家住后排,或凭抓阄或相互协商决定。
宅基地定下来,接着就是修路与清障。那会儿经济条件差,农庄线的路自然修土路。光有新路还不行,还得打通通往新宅的通道,砍去挡路的树木、清理路边的杂草、填平坑洼的沟塘。只有通道平坦了,抬屋时才能走得稳、走得顺。
接下来就是腾房,请能工巧匠“做撬”。那时候家家都穷,没多少家当,先搬的人家就把物件寄放到后搬的邻居家里。做撬是个技术活儿,要抬的都是茅草屋,四面是芦柴障笆,也偶有局部砖墙的。做撬时,工匠选用碗口粗的毛竹,纵横交错,固定在房柱约大半人高的位置,再用生麻绑扎撬紧,形成“井”字形方格。每个方格约有三四张方桌那么大,能站七八个人。
抬屋的多在农闲的冬季进行,既不损坏庄稼,又有充裕的人力。具体时间由生产队长和户主商定。若要抬的房子多,便集中人力,一户接着一户抬。
抬屋最热闹、也最惊险的要数起抬和移动环节。抬屋开始前,队长或他人会提着一面筛子般大小的铜锣,爬上屋顶,使劲敲击,向人们发出集合的信号。锣声就是命令,村里的青壮劳力不论男女,听到锣声,不管多忙,都会放下手上的事情,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这时,主人通常会手捧面盆或系着围裙,里面装着一分钱一块的糖,还有廉价的“勇士牌”或“经济牌”香烟。见到来人,抽烟的发烟,不抽烟的发糖。这便是主人对每个抬屋人的款待和答谢。
抬一座三间的屋子,需要两百多人。此时的队长胸挂口哨,手执红旗,拿着铁皮喇叭,俨然成了一名指挥官。他先安排青壮男子站到屋子四个角落等关键部位,待所有人各就各位后,便开始发号施令:“大家注意!为防止发生踩踏,一定要抱紧杠子,脚下踩空也不能松手;把鞋带系紧,鞋掉了也不能捡!屋抬起身后要等拨正了方向才能起步……听清了没有?”哨声响起,随着“起身”令下,人们挺起腰杆,房屋缓缓悬空而起。原地调整方向后,大家铆足劲,迈着沉稳的步子,跟随红旗的指引齐步前行。
抬屋最重要的是步调要一致,否则容易乱了阵脚。“嗨哟、嗨哟”的号子震天响,众人踩着号子的节奏,一座老屋就像一辆慢行的大巴,缓缓地朝着新的宅基地行进。距离不远的一次到位,距离远的中途会休息一两次。
房子抬到了新宅基地,不管多累,抬屋的人都不能直接把房子撂下。这时队长已把现场指挥权交给了木匠师傅。“向前一步走!”“向西退两步!”人们按照他的口令,抬着房子在场地上缓慢移动,校正到位后,木匠师傅一声“落地”,大家才顺着劲儿轻轻放下肩上的房子。后续的卸杠、整修等工序则交由专门的人去完成。
在主人的答谢声中,大汗淋漓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纷纷散去。抬屋的人多数是本队的,抬大屋的时候也有邻队派人支援的,甚至还有路过的陌生人也加入到抬屋的队伍。抬一次屋每人也就得到三四分工,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互帮互助,助人为乐。
抬屋并非总能顺利完成,也有失败的时候:有的因为选址未充分征求农户意见、不够科学,导致农户不愿搬迁,进而拖延工期;有的则因为抬杠没绑扎牢固,中途松了撬,屋子晃悠着散了架,只能拆了重建。
抬屋的场景已成为记忆,并渐渐被人们所淡忘。别小看这抬屋——它既能体现组织者的谋划与动员能力,也能映照出干部与群众的关系,甚至还可以折射出一方的村风民情。
如今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再也听不到抬屋那震天的号子声,见不到上百号人抬着屋子齐步向前的壮观场面。然而,那些大汗淋漓的脸庞、踩着号子的脚步、递糖递烟的温情,还有众人齐心合力的那股劲儿,都像老屋的梁木一般,深深扎根在一代人的乡村记忆里,成了一份朴素而温暖的怀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