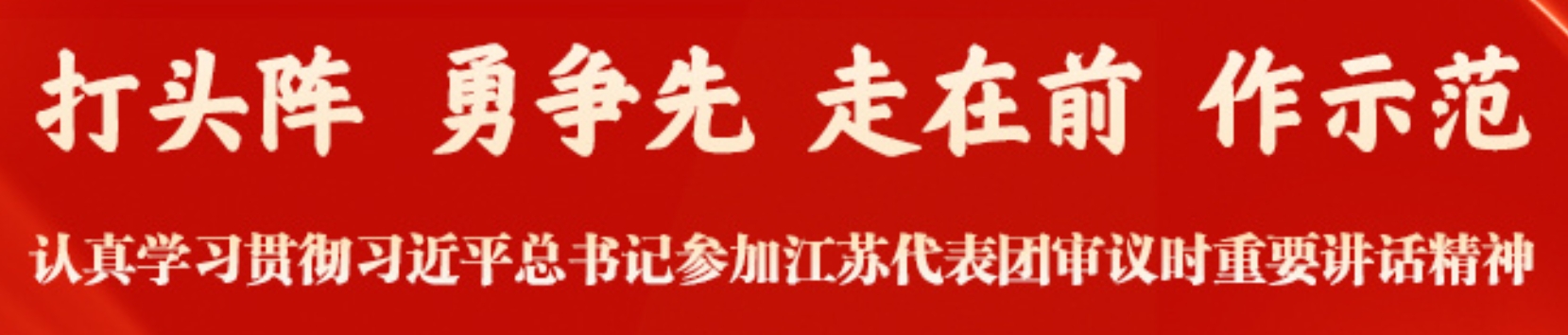父亲的桑木扁担
老家屋后曾有一棵桑树,自我记事起就扎根在那里。碗口粗的树干,枝繁叶茂。每逢夏日,树上便缀满紫黑的桑葚。我和几个小伙伴,像猿猴一样攀援而上,骑坐在枝丫间,争着采摘,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,直吃得唇齿尽染,衣衫斑驳,才心满意足地下来。
有一天放学,我蹦蹦跳跳地回到家,发现屋后空荡荡的——桑树不见了踪影!只剩下一截两厘米高的矮桩子,默默地在那里诉说着它的遭遇。我走进堂屋,看见有一条黄澄澄的扁担倚靠在墙角,上上下下皆呈现出刚刚刨过的光泽。母亲说:“你父亲找人把树砍了,做了一条扁担,说是结实,干重活时需要它。”
那时,我懵懂无知,只惋惜失掉了嬉游的乐园,尚未能领会这扁担可以取代鲜活的桑树,担起全家未来的希望。
第二年,我考取了当地的一所完全中学。开学那天,晨曦初露,母亲就帮我收拾好行李和几本杂书。父亲拿起那条桑木扁担和一副泥笿儿,一头装着旧木箱,一头坐着我。月亮还明晃晃地悬挂在静静的夜空,微风轻柔地吻着我的脸颊,路边杂草上的露珠似乎在向我眨眼睛。父亲走在乡间小道上,扁担随着步伐在微微晃动,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只听见父亲低声哼着我熟悉的号子,就像唱着一曲非常动听的歌谣。我的双手抓着泥笿的绳索,抬头看见月光涂抹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,他的背影在我仰视的角度下,显得格外魁梧高大。
我心头一热,猛然醒悟:父亲的这条桑木扁担,还挑着对我的殷切期望。
我们兄弟姐妹多,家里一直不宽裕。寒假过后,我初一第二学期的学费还没凑齐。父亲出早工回家,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币,我发现他的鼻子下面还留着未擦净的血痕。母亲怏怏地说:“家里钱不够,想向贲山勇借钱。他开玩笑说:‘寿爹,你能把一担泥和两个妇女挑上河岸,我送你五角钱。’你父亲虽然力大如牛,但这么重……”父亲赶忙接过话茬:“别说了,我心里有数。这不是挑上去了吗?”母亲眼里噙满了泪花,她拿了一条旧毛巾,让父亲擦了擦脸。我又气又心疼,转身找到那条桑木扁担就要向贲山勇家冲。父亲急忙追上我:“闹着玩的,不准当真。回去……”我害怕父亲生气,只好作罢。但我把父亲借的钱交给了母亲,让她瞒着父亲,过几日再还给山勇。然后,我向王叔叔借了五毛钱,才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
路上,我默默想着:父亲为了我几毛钱的学费,竟用他那条桑木扁担,不动声色地挑起了尊严之外更沉的东西。
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,我去上河工挑泥。天寒地冻,河底流沙如刀,我们赤脚踩在冰碴里掘泥。父亲和我在一个断面上,他见我卷起单裤,腿脚红得发紫,浑身瑟瑟发抖,二话没说,就用他的桑木扁担套上我的筐绳,悠悠地放到自己肩上。自此以后,每一担泥,都是父亲从河底挑到河岸,我再接过去送上圩顶。他的身影在寒风中移动,桑木扁担深深嵌入了他那耸起的肩胛。
桑木扁担的韧性很强,它挑着泥土与父爱的双重重量。我知道它是在以独特的方式,为我挑走人生最初的风霜。
后来,父亲染上了肝病,却仍然强撑着下地割玉米桩子。那时我十九岁,在村小做民办教师。秋阳高照,中午放学,我走到田间,见父亲艰难地挪动脚步,佝偻的背影让我鼻子一酸,眼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。我一把接过父亲的桑木扁担,语气坚定:“您有病,年纪也大了,让我来挑。我年轻,有力气……”两担就把所有桩子都挑回了家。说实话,有些吃劲。父亲见我的脚步有些沉重,很是心疼。他说:“你当老师,少干重活,下次还是我来吧!以前……只要桑木扁担吃得消,我就不会认输。如今病了,力气不比当年了……”他长叹一声,眼里闪动着泪光。
我扒了两口饭就赶回学校。课间如厕时,竟发现小便带血。我慌忙去大队卫生室,徐医生说是用力过猛,毛细血管破了。
此事我一直瞒着父亲,就像他曾经瞒过我许多苦楚一样。那条桑木扁担太沉,我们父子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独自承受。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。今年农历七月半回老家祭祖,我又在堂屋角落里看见了那条桑木扁担——它已历经沧桑,枯黄发暗,中间一段曾被父亲的肩头磨得油亮,而且微微凹陷,恰如岁月凝固的印记。
我将它捧在手中,仔仔细细地端详:木纹有些粗糙,就像当年我们吃的糁儿饼;轻轻抚摸,仿佛还残留着父亲的体温。倏然间,我老泪纵横……
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桑木扁担:它一头挑着对儿女的关爱,一头挑着家庭的重担;它承载了一个农民沉默而坚韧的一生。
如今,桑树依然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茁壮生长,我触摸到的不再是甜美的桑葚,而是比果实更厚重、更甘醇的传承与担当。
啊!父亲的桑木扁担,原来就是他挺立一生的脊梁!(徐其白)